
红色记忆
人文贵医
校史
师
编者按
贵州医科大学创立于抗日烽火之中,成长于新中国五星红旗之下,发展于奋进的改革年间,壮大于新世纪初年,奋进在美好新时代。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回望学校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探寻贵医血液中流淌的红色基因。守正初心,始终不忘来时路,思创未来,坚实迈进新时代!


李宗恩小传

李宗恩(1894—1962),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汉族,医学博士,1948年当选中国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早期热带病学专家及著名医学教育家,国立贵阳医学院首任院长,后曾任北京协和医学院首任中国院长等职。

青少年时代的李宗恩(左)
李宗恩博士出生于清末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父亲李祖年为甲午年(1894)恩科进士,后被钦点为翰林庶吉士,曾任山东的知县。李宗恩幼时即就读于其父亲所开办的新式小学,后来进入上海震旦学院(1932年改称震旦大学)学习法文。
1911年夏季赴英国留学,初入预备学校,随后进格拉斯哥大学医学院,1920年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后赴伦敦大学卫生与热带病学院担任蠕虫病助理研究员。
1921年4月至9月参加英国皇家丝虫病委员会赴西印度考察热带病,随后任职于格拉斯哥西部医院,1922年1月获得伦敦卫生及热带病学院颁发的卫生及热带病学硕士学位,1923年回国。
1923—1937年任职于北平协和医学院,其间定期赴江南考察热带病疫情,进行防治和研究。
1937年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即接受国民政府教育部之聘,南下筹办国立贵阳医学院,并于1938年3月成立后担任第一任院长职务。在以后的近10年里,李宗恩院长领导了贵阳医学院的早期建设和发展,直至其成为一所完备的现代医学院校。
1947年5月李宗恩奉调北平担任协和医学院院长。1948年因对医学教育作出卓越贡献获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荣誉博士称号。
20世纪20—30年代李宗恩主要研究寄生虫病,尤其是丝虫病、血吸虫病、疟疾和黑热病,先后在国内外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共18篇。他曾在华北、华中地区设立血吸虫病及其他多发性热带病的病情观察站,是中国热带病学研究的创始人。后期投入医学教育事业,造就无数医学界人才。毕生从事医学教育、科研工作,对血丝虫病、血吸虫病、疟疾和黑热病等有较深研究,在黑热病流行病学研究工作中尤有建树。
李宗恩与贵阳医学院

对于李宗恩先生,许多人对他的了解更多的是北京协和医学院第一位华人院长,但作为国立贵阳医学院(现贵州医科大学)的筹备委员会主任和首任院长,在贵医的9年中,他对贵州医学高等教育及医疗事业的发展却起着重要的作用。
1937年7月,日军炮轰宛平城。国民政府教育部王世杰部长邀请北平协和医学院李宗恩等人筹建武昌医学院,“八一三”以后,抗战全面展开。经淞沪血战,上海沦陷。战线随之西移,抗战形势趋紧。教育部决定将正在筹备的武昌医学院改建到更为安全的大西南,成立国立贵阳医学院,以接纳从华北及其他敌占区退下的医学院学生。
12月31日,教育部聘李宗恩、朱章赓(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公共卫生专家)、杨崇瑞(协和医院妇产科专家、国立北平第一助产学校校长)为国立贵阳医学院筹备委员,指令李宗恩为筹备主任,又聘为国立贵阳医学院院长。宗恩毫不踌躇地接受了这一千头万绪正无从着手的任务。1938年1月1日,李宗恩在汉口成立国立贵阳医学院筹备委员会。教育部加聘张志韩 (原任贵州省教育厅厅长)和杭立武(在教育部任职)二人为筹备委员。在汉口实际负责筹建工作的还有原武汉大学生物化学教授汤佩松等,到贵阳后还得到原贵州省省立医院院长朱懋根的大力协助。
几经辗转,初具规模

1938年1月10日,国立武昌医学院筹备委员会在汉口召开了第三次会议, 李宗恩、金宝善、王星拱、黄建中、周天放(尹天动代)、杨崇瑞、汤佩松、朱章赓等出席,其中李宗恩为主席,他报告了教育部关于武昌医学院暂停筹备,所有权及经费由国立贵阳医学院移拨借用的指令。接收国立武昌医学院筹备委员会经费36941.07元,接收国立北平第一助产学校武昌办事处,聘请教师,招收学生等事项……筹备委员会就这样如火如荼地开展工作了。
2月中旬,宗恩由汉口经重庆转道来贵阳在禹门路133号设立国立贵阳医学院临时办事处。
3月1日,救济流亡之学生学业,树立西南医学教育之基础的国立贵阳医学院正式成立。租赁虎峰别墅王公馆、三圣宫等为临时校舍。定制、调拨和采购所有教学设备,包括课桌椅,因陋就简的实验仪器、图书等等。同时李宗恩利用其在协和任教的14年,医科、药科以及某些前期或后期临床的课程,聘请协和1926-1934年间各级毕业生担任。他还请到了自北方南撤的几位名教授担任前期的基础课。宗恩的一个好办法就是放权,聘请了各科系的主任后,就由他们自己去物色适当的人选。在汉口、重庆、长沙、西安、贵阳五处设立招生处,共收容战区退出的失学医学生及护士助产士学生计300余人,他们来自30余所院校。学生们年级不同,学业参差不齐,故采取分班教学,五个年级,九个班级,课程照旧,同时开课,按时毕业。
6月1日,贵阳医学院如期开学。在此期间,李宗恩把他的亲弟弟李宗瀛从原单位调出,助他应急应变,并坦率地告诉他,因为是他的弟弟,所以在创业中,要做得多拿得少。并派他去押运第一批物资,这批物资走水路由汉口到重庆,再由公路运抵贵阳。
贵医初具规模,除了教育部规定的课程设置,还设立了“人文科”(Humanities), 开设语言、文学、哲学、逻辑等课程,为的是扩大医学生的视野。
当时主持这一科的是留德专攻康德哲学的洪士希(洪谦)教授。在宗恩自己撰写的贵医院史中,洪谦博士名列教授名单之首位。这是因为贵医的科目是按人文科、基础学科、临床前学科和临床学科的次序排列的。在人文科的科室会议中,李宗恩总是带头参与并积极参与讨论。
在李宗恩的心目中,人文科目绝非可有可无,它应该居于先行的位置。
化育人才,弦歌不辍

李宗恩对新医学的理解是:人是一个整体,在战胜疾病的过程中,心理因素起着不小的作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完全依靠药物来对付某些症状,是等而下之的方法;细心的护理应该包括帮助病人建立信心,有了战胜疾病的信心,药物就能起更好的作用。贵医率先在全国医学院校中开设心理学等,后来得到教育部的推广。为推广新医学,反对落后与愚昧,宗恩邀请其弟妹编了个宣传新医学的话剧。演员都是医学与护士班的学生。演出那天,当宗恩作为群众演员走上舞台时,气氛真是热烈。戏本身的粗糙全被他的人格魅力遮住了。该戏后来经过专业人员的修改,假期里还去重庆演出过。
李宗恩认为,贵医要让医学科学在西南扎根,关键在于赢得那个贫困落后的社会对它的了解、信赖和接受。临床是医学院教学的重要组成。在此以前,学生的教学实习和临床实习都有赖于省立医院。
1941年,为了让贵医有临床教育,李宗恩和杨济时筹集了部分资金,在贵阳市阳明路两广会馆,因陋就简,设10张病床,成立了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由杨济时任院主任。医学从来都是严谨刻板,乃至冰冷的,加之物质匮乏,生活艰苦,为消解学生日常生活里的冗繁,干枯与琐碎,李宗恩居然组建了一支口琴队!用节省下来的院长办公经费,在香港订购了各型口琴。
经过训练,没过多久,什么《比翼鸟》《双鹫进行曲》《汉宫秋月》等乐曲,都不在话下,还定期在贵阳市内和电台公演,成为贵阳最有名的口琴演奏队。继而他又建立了话剧队、国剧队。前者,为贵阳市捐献慰劳筹款公演,自己还参与《叔叔的成功》等剧目的演出。后者,为劳军、赈灾、募捐等义务也演出多次,剧目包括《玉春堂》《武家坡》等。风流尽显,旧时代一个受教育充分的知识分子在文化上的深度以及个性之饱满充盈,令人感佩。
几年下来,在西南边陲,于荒僻之地,李宗恩等一流教授以血水奔流的方式,培养出合格的医科学生,由是激发出人们在战争中拯救生命的热望。化育人才,弦歌不辍。这所原本不为人知的贵阳医学院,在硝烟中越发显得崇高和厚重,引得燕京大学司徒雷登等人也来贵阳参观。有如一条缓慢的水流因高压而成为壮观的喷泉,在战争阴暗的缝隙中迸射出一线夺目的光亮!
转眼到了1944年的冬季,日军节节西进,由广西逼近黔省,贵阳一夕数惊。省政府命令各机构和市民疏散,贵医决定迁往重庆歌乐山。
据学校一位技术员回忆:“临走那天, 李宗恩对前往重庆的师生说,同志们、同学们,我们还会再回来的。”在场的人已是泣不成声。贵医才撤了一部分到重庆,战局就有了转机,日军在独山受阻。
于是,贵医的另一部分就留在了原处。
苦难坚持,重振旗鼓

日军投降了,贵医的去向就变成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撤至重庆的那部分,借用的是上医在重庆的校舍,复员在望,上医在教育部的支持下,提出了接管贵医的要求。这样,战争一结束,上医迁回上海,贵医就名实两亡了。
当初创建贵医时有两个明确的目的:第一是收容来自战区的医学生,为他们创造条件,完成学业,成为国家急需的医务人员;第二是建立一个地区性的医学院,为发展这一地区的医药卫生事业培养人才。到40年代初,第一个任务已接近完成。而第二个任务上升为首位。如果把贵医并入上医,迁往上海,贵医多年为提高落后地区医疗水平所作的努力就落空了。为此,宗恩力主将贵医留在贵阳。经过万般艰难,贵医终于在贵阳重整旗鼓了。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教育部决定在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和武汉大学分别增设医学院。
1946年3月李宗恩参与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医学院筹备。筹备工作开始不久,李宗恩因受聘为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并主持协和复校工作,武汉大学附属医院先行筹设,由原贵医外科教授杨济时大夫负责主持,并推荐贵医王季午教授主持浙江大学医学院的筹备工作。
在战火中遭遇苦难,在苦难中坚持不懈,国立贵阳医学院以“永远独立”的风姿完整地保存下来。在贵医的9年,作为一个医学教育的拓荒者,宗恩几乎放弃了自己最热爱的热带病学研究,推行公医制度,保障边民健康,提倡健全生活,他为贵州乃至中国的医学事业作出很大的贡献,也承受了许多周折乃至误解,但他懂得作为一个院长的第一意义, 就是负担起自己的责任。
那次贵阳上演一部美国电影《万世师表》,片子的原名是《再见吧,契普先生!》。契普先生一生没有什么惊人之举,有的只是献身教育的决心和关心学生的诚挚之情。散场时,贵医的学生把他们的校长围在影院前的广场上,迟迟不肯散去。

来源:党委宣传部新媒体中心
图文:整理自《敬往思来—贵州医科大学八十年文史集萃(1938-2018)》
排版:吴克州
编辑:李菡逸 李牧
审核:陈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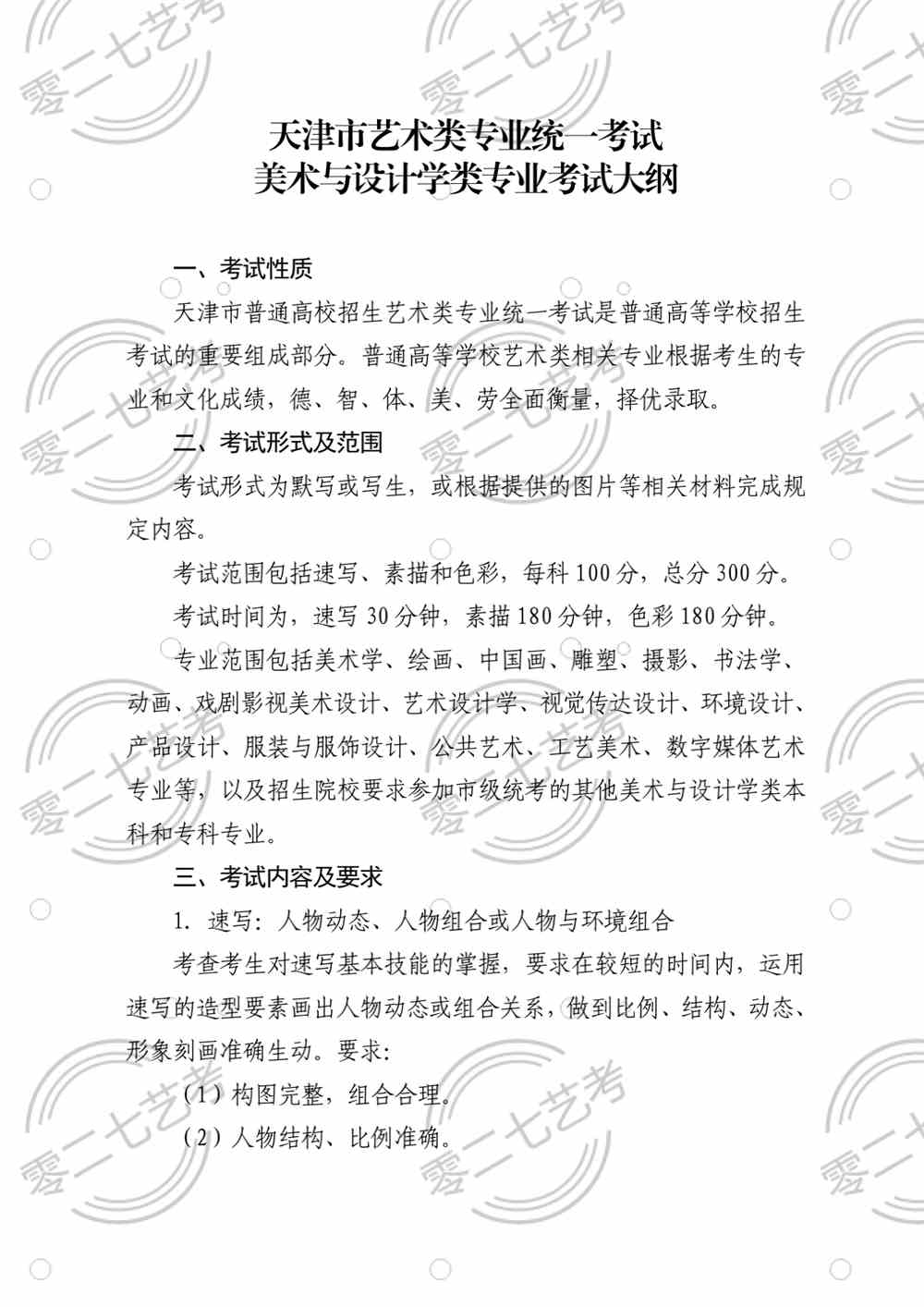







艺考用户说说
友善是交流的起点